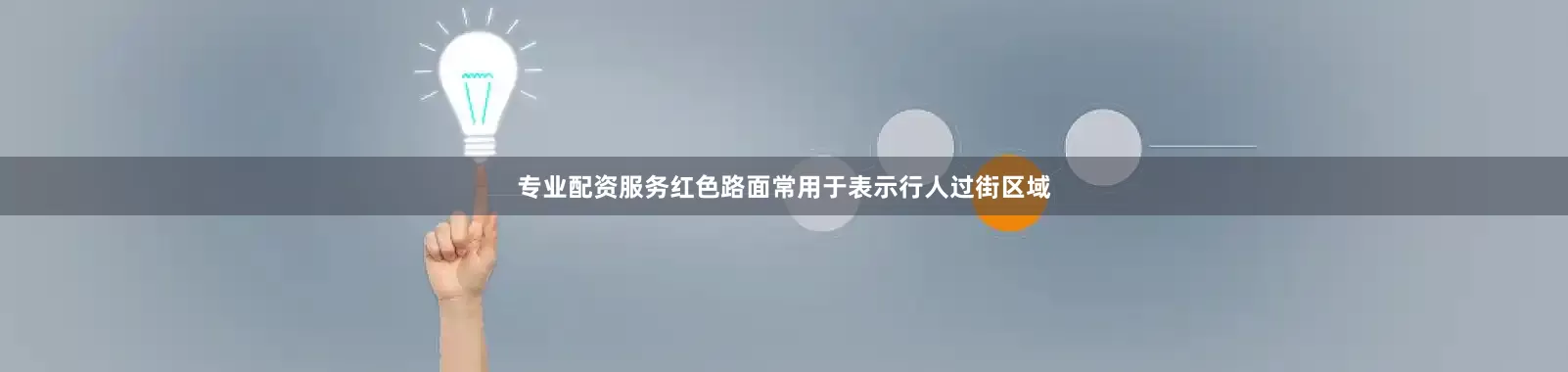1982年4月26日,地点位于桂林恭城县。那天下午,天空笼罩着细密的雨丝,阴云低垂,整个恭城县的山峰在灰蒙蒙的雨雾中若隐若现,仿佛被黄昏的暗影提前覆盖。雨中的大小山峰显得格外幽暗,笼罩着一层沉重的肃穆气息。
这个湿冷且迷雾弥漫的春日下午,村民们大多选择待在家中。距离桂林奇峰机场仅有45公里的恭城县,也被这层厚厚的雨雾笼罩着,安静得几乎听不到任何声音,仿佛沉睡于这连绵的细雨之中,周围一片肃静。
谁会想到,就在这一个平凡的春日午后,在人们沉浸于慵懒与困意的眼神里,忽然一声刺耳的“轰隆”巨响划破了静谧,犹如一把利剑刺破了阴沉的天空,瞬间打破了整个午后的宁静。那震耳欲聋的声音瞬间将人们从慵懒的春困中猛然拉回现实。
展开剩余90%尽管屋外依旧细雨绵绵,大家顾不得雨水纷纷走出屋外,望向远处被浓雾遮蔽的群山,希望找到声响的来源。然而,厚重的雨雾使视线变得模糊,什么也看不清,只能感受到那空中回荡的巨大轰鸣提醒着每个人:这里发生了异常,心头的不安和预感如阴云般紧紧笼罩。
几天之后,当地人终于得知,那个下午传来的巨响竟是3303次航班B-266号飞机在距离桂林奇峰机场45公里外的恭城县上空坠毁的声音。机上104名乘客和8名机组人员无一幸免,全部遇难,惨剧令人心碎。
这架飞机隶属于空军第34师第100团,机长是五十多岁的副团长陈怀耀,副机长则是年仅32岁的飞行员陈再文。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是当日恭城县上空浓雾弥漫,能见度极低。飞机下降到1400米高度时,机长突然发现眼前竟是一座海拔接近1500米的山峰。
机组人员,包括副机长陈再文,都目睹了这极其危险的局面,急忙尝试拉升飞机避免撞击。可就在此时,山谷中突发强烈的风切变,使飞机无法完成必要的爬升动作。最终,飞机失控撞向高耸的山峰,瞬间燃起熊熊烈焰,整架飞机被摧毁成碎片。
这场空难异常惨烈,尤其引人注目的是遇难者中副机长陈再文的身份——他是开国上将陈锡联的儿子。当这噩耗传到陈锡联将军耳中,中央领导特派工作人员前往其家中慰问,并希望老将军能做好家中亲人的思想疏导。
此时,年近七十的陈锡联强忍着失去爱子的沉痛,平静地对工作人员说:“我这辈子经历过无数生离死别,战争年代有牺牲,和平时期也同样难免。你们告诉中央领导,家里其他人的事由我来承担,让大家放心。”他的语气中虽有沉稳,却掩盖不了深深的哀伤。
看着这位老将军坚定的眼神,众人无不心生敬佩,紧紧握住他的双手。这双布满老茧、饱经风霜的手掌,给予人坚强的力量和温暖。然而在坚强的表象下,陈锡联那布满皱纹的眼角依然湿润,轻轻叹息声一次次流露出他内心的悲痛难以言说。
陈锡联一生正如他自己所言,经历了太多的生死离别。年轻时第一任妻子早逝,儿子又夭折。如今,风烛残年的他,再度承受失子之痛。亲人的一再离去,怎能不令人心碎?
1915年,陈锡联出生于湖北省红安县的一个贫苦家庭。父亲早逝,母亲与他相依为命。年幼的他经常帮家里干柴草、种地、给地主放牛,做尽了辛苦活儿。
十四岁那年,听闻游击队经过家乡,怀着一颗为穷苦人打天下的决心,年幼的陈锡联毅然报名参军。游击队因他年龄太小而拒绝,但他的执着打动了战士们,他一路跟随游击队,最终被接受。
不久后,他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的一名光荣的小红军战士。虽然年纪小,大家最初都怀疑他的能力,但他刻苦训练,聪明勇敢,几次战斗中总是冲锋在前,赢得了大家的认可。
因为表现出色,陈锡联先后加入共青团和中国共产党。1931年,年仅16岁的他被提升为连队政治指导员。真正让他声名大振的是1937年10月,率领129师在山西代县掩护群众,夜袭日军阳明堡机场。
10月19日夜,陈锡联带领129师769团战士,仅用不到一小时,消灭了100多名日军,炸毁24架军用飞机。这场战役切断了日军的交通运输线,成为当时国内外的重大新闻。蒋介石特颁嘉奖令,769团被誉为抗战四大名团之一。
此后,陈锡联从八路军团长一路升任副旅长、旅长,最终成为军分区司令员。在夜袭旧关镇、平汉路破袭战等战斗中,他屡立战功,被誉为当代赵子龙。
在战争岁月中,他也收获了爱情。1942年在延安抗大学习期间,认识了毕业生黎芝慧,二人相知相恋,1942年12月结婚。三年后,他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儿子。
然而幸福短暂,1948年秋天,黎芝慧因病去世,留下三岁的孩子和孤独的陈锡联。尽管生活艰辛,他依然努力安排好生活和工作。每当听到孩子喊出第一声“爸爸”,他便感动落泪,想到早逝的妻子,心头泛起阵阵叹息。
次年,他被调往上海工作,结识了王璇梅——陈赓妻子的妹妹。陈赓一向视王璇梅如亲妹妹,曾嘱托她专心学习。毕业后已27岁的王璇梅来到上海,陈赓觉得该为她介绍一位合适对象,于是促成了她与陈锡联的见面。
初次见面,王璇梅对有能力、忠厚且有英雄气概的陈锡联颇为满意,但陈锡联性格腼腆,行动迟缓。陈赓催促他主动,随后两人开始约会,很快情感深厚,结为夫妻。
婚后,王璇梅将黎芝慧的孩子视若己出。然而,这个乳名“黑娃子”的孩子不幸早逝,陈锡联再次经历丧子之痛。幸好有王璇梅的陪伴和安慰,他慢慢走出阴霾。
1950年,他们的第一个亲生孩子出生,取名陈再强,寓意希望孩子坚强成长,代替早逝的哥哥。1951年,第二个孩子陈再文出生,他与父亲陈锡联无论外貌还是性格都极为相似。
1959年国庆十周年庆典上,毛主席首次见到陈再文,笑言:“这父子俩是一个窑里烧出来的。”新中国成立后,陈锡联不仅重拾家庭幸福,还想着接在乡下的母亲到城里享受儿孙绕膝的晚年。
回忆起担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三纵队司令员时回家探望母亲的情景,他看到母亲满头白发站在破旧木门前,泪水夺眶而出,跪倒在母亲面前。母亲阻止他下跪,说:“一个司令员,怎能在众人面前给老太婆下跪?”那一刻,母子俩泪流满面。
尽管誓言解放后接母亲到城里,但母亲因习惯了农村生活,最终拒绝随他离开。陈锡联此时已被毛主席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员,工作繁忙,数年未能回乡探望母亲,幸好母亲身体尚健。
他的四个孩子各有成就:大儿子陈再强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,逐步晋升为沈阳军区后勤部40分部部长;二儿子陈再文成为光荣的空军飞行员;三儿子陈再方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,后来任总装备部综合计划部局长;女儿陈再红则成为人民教师。
孩子们均表现优异,陈锡联心中满是感激与幸福。可是1982年4月26日,这一天成为他永生难忘的痛苦记忆。二儿子陈再文那声巨响,带走了他生命中最后的慰藉。
在无人的深夜里,陈锡联常常梦回那一刻,浑浊苍老的双眼茫然无神,难以接受儿子的离去。然而,他深知新中国建设充满辉煌与泪水,牺牲难以避免,唯有从中吸取教训,期望悲剧不再重演。他默默流泪,选择坚强面对。
1985年,陈锡联在福建前线执行任务时,收到家乡姐姐的信,告知母亲病重。他因公无法立刻回家,只得等任务完成后匆匆赶回。抵达时,只见母亲冰冷的墓碑,耳边传来秋风中枯树断草的悲鸣。
跪倒在母亲墓前,泪水如雨下,哭声哽咽。他这辈子,青年时期丧妻失子,晚年再遭丧子之痛,继而母亲离世,悲痛如山。正如他说的,他见惯了生离死别,坚强只是表象,痛苦藏于心底。
有人劝他写自传,他淡然回应:“红军时期和我一起打天下的两千多人,现在只剩十几人,我算什么?”但年岁渐长,思念更深,他泪眼婆娑,用笔记录那些往昔的深情与回忆,仿佛又回到了那个铁马金戈的战场岁月。
那时的他英姿勃发,智勇双全;然而一生的离别和痛苦早已镌刻心头。如今亲友渐远,年事已高,他仍有无尽话语,却不知该与谁倾诉。
发布于:天津市配资企业排名前十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